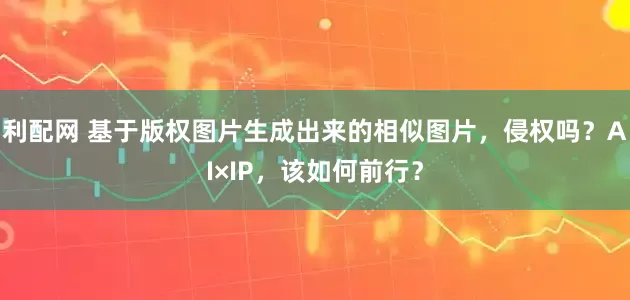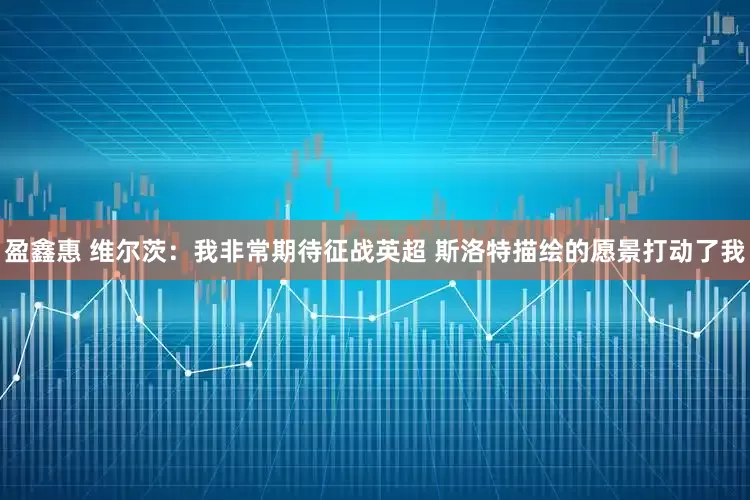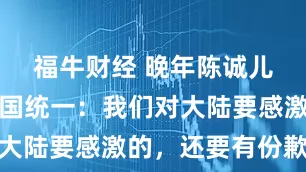
“1988年冬天,你怎么看统一这件事?”朋友刚踏进台北敦化南路那间老宅,就抛出这个问题。陈履安把手里的茶杯轻轻搁在桌上,顿了顿:“要感激,也要道歉。”他把这十二个字说得很慢福牛财经,仿佛要让每个音节都落进对方耳朵里。
这句话背后,藏着两代人对海峡两岸的不同理解。要弄清缘由,得把时间拨回到1924年。那一年,黄埔一期结业的军官刚刚披上大檐帽,台上训话的蒋介石在人群里锁定了一位身材并不起眼的青年——陈诚。就在同年秋季,蒋介石亲笔写下“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”,一句戏谑的口头禅,却奠定了两人此后四十年的政治命运。

抗日战争期间,陈诚先后坐镇淞沪、武汉、四川,忙到连家里孩子的牙掉了都不知道。淞沪会战后期,他在前线指挥时腹痛到弯腰,军医诊断是十二指肠溃疡,必须手术。陈诚一句“等打完这仗再说”,又硬撑了三个月。陈履安后来回忆:“小时候见父亲最多的场合就是车站月台,他总是匆忙下车,又匆忙上车。”
1947年夏,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。辽沈战役爆发,蒋介石电令陈诚赶赴东北“力挽狂澜”。当时陈诚病情加重,体温持续39度,副官都劝他别去,他只回答两个字:“能走。”几个月后,锦州失守、长春告急,陈诚终于扛不住,住进上海陆军总医院。北平的记者写出尖锐评论——“杀陈诚以谢天下”。在这种压力下,陈诚被解除全部职务。病房外墙涂着灰色油漆,他侧身看窗外,给秘书口述:“短期形势不妙,长期未必无望。”

1949年12月,国民政府全面迁台。蒋介石没有选择任何一位深得南京要员的心腹,而是让刚脱离病榻不久的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。陈诚明白,这是最后的政治考卷:一面要养活近两百万跟随而来的军民,一面得筑起“反攻大陆”的基地。那一年的台北福牛财经,下着连绵冬雨,台糖仓库里堆满白米却缺少运输车辆,街头小贩拿着麻袋装钞票却买不到一双布鞋。物价指数数据每天往上跳,没人知道明早一碗阳春面的价格。
陈诚采取了三个动作:一是币制改革,二是军队整编,三是“三七五减租”。先说第一项。1950年6月15日,台湾当局宣布旧台币一万换新台币一元,同时限期收兑。为防止失控,他向财政部门调拨八十万两黄金做背书,来源正是当初自南京、上海等地转运的国库储备。陈履安日后直言:“如果没有那批黄金,新台币撑不到一个月。”这也是他日后坦言“感激大陆”的缘由之一。
接下来是军队整编。蒋介石要求原番号照旧带枪进岛,陈诚却主张“先缴枪再编制”。彼时,数十万退败官兵情绪低落,谁都不想缴械。陈诚提前放话:“进港先下船,第一步交武器。”码头上堆成小山的枪械堪比军火市场,他顶住骂名,才避免了岛内派系林立、枪声四起的局面。此举固然得罪了许多旧部,可换来了台北、台中、台南难得的治安喘息。

第三项是“三七五减租”。1949年台湾总耕地约一百一十万公顷,佃农租比高达五成。大陆教训还历历在目,陈诚认定:不动到土地制度,经济稳定就是空话。1951年春,他通过命令把田赋比例强行降为37.5%,地主们集体抗议,甚至出现抬棺材游行。他夜里批阅电报,面对秘书只说一句:“迟早要动刀,早点痛快。”政策落地的第一年,岛内水稻总产量立刻增加近一半,原先倾向闹事的民众倾向悄悄在家加盖厨房。
值得一提的是福牛财经,陈诚始终避免在公开文件上出现“反攻大陆”字样。他知道蒋介石视此为一生心愿,却也清楚现实条件根本不允许。1965年3月,陈诚病危,口授六十六字遗言,句句提到“团结”“共患难”,唯独没提“反共”“反攻”。蒋介石初听草稿时沉默良久,还是同意保持原文。
同年十二月,陈诚病逝,终年六十七岁。出殡那天,台北到阳明山交通几乎瘫痪。陈履安站在灵车旁,抬头瞥见山坡上插满青天白日旗,心底却另有一番思量。二十年后,他进入政坛,被视为“跨党派的温和派”。1986年,他公开表示:“两岸终需坐下来谈,而我们对大陆除了感激,还有歉意。”那份歉意指的是什么?陈履安私下解释过两次。

首先是黄金。他说,1948年底短短两个月,国库共调走三百九十万盎司黄金,占当时库存六成以上。本意是“反攻资金”,却最终成了在台湾发行新台币的信用支撑。他做过粗略折算,若按九十年代金价,那笔资金已达近百亿美元。正因如此,他改口称其为“大陆对台湾的无形贷款”。其次是人才流失。内战尾声,大批技术官僚、大学教授随军赴台,导致大陆若干研究所和大学陷入师资断档。陈履安自嘲:“我们把别人家粮食和先生都搬来,还常说自家勤劳致富,难免尴尬。”
也因此,当岛内掀起“去中国化”浪潮时,陈履安选择站在反对一边。他在政论节目说:“没有大陆,台湾只能被迫回到捕鱼晒盐的农业社会。历史事实摆在这,没有谁欠谁一辈子,也不能抹掉互相成就的部分。”现场来宾一度冷场,主持人只得转移话题。
陈履安的立场并非空穴来风。1987年开放探亲后,他三次申请赴大陆,都因“政坛敏感人物”被拖延。1993年,终于踏上厦门码头。他找到父亲旧日的部下、已经改任地方官的老兵。对方递烟说:“老陈走得早,可你来了就好。”两人对视半晌,无言。后来他回忆,那一包本山烟的味道混着海腥气,让他第一次真切体会“同胞”二字。

与此同时,台湾经济从六十年代出口导向转向高科技,早期积累的黄金、土地改革及低成本劳动力是原始资本,外加二战后美国的大规模物资和技术援助,造就“亚洲四小龙”神话。陈履安反复强调:“这套组合拳里,包含大陆的无声贡献。”不少媒体批评他“唱衰自己”,他却说:“历史不能只写一半。”
对于统一,他用过一个比喻:“两岸像拆散多年却血脉相连的兄弟,先认祖再细谈家产。我的父亲那一代带枪讲话,不成功;我们这代得放下枪,用账本、用记忆、用常识谈。”说完,他幽默补充:“账本可别翻到最后一页,黄金那笔欠条还在。”

细看陈诚一生,从黄埔课堂到台北官邸,他一直活在蒋介石阴影里,却也用自己的逻辑尝试修补残局。土地改革救了台湾乡村,币制改革稳住了市场,军队整编减少了派系火并。倘若没有这些动作,蒋介石的“复国基地”能否维系十年都难说。但人们往往忽略另一面:这些动作背后,依赖的仍是大陆的黄金、物资与血缘纽带。换句话说,没有抗战八年积累,也没有内战末期的大规模迁徙,台湾的后续奇迹恐怕要大打折扣。
如今,陈履安那句“感激与歉意”在岛内依旧是小众声音,可它像一颗钉子钉在木板上,拔不掉,也生锈不了。对岸的灯火、海峡的潮汐、档案里的数字,都在提醒人们:历史不是黑白棋局,而是一张复杂的拼图。谁拿走哪一块、又补回哪一块,日子久了,总要算清。问题是——我们准备好那张完整的拼图了吗?
七星配资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